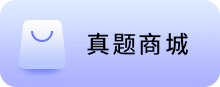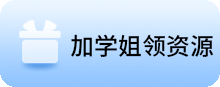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西方音乐史简介的内容如下,更多考研资讯请关注我们考研派网站的更新!敬请收藏本站。或下载我们的考研派APP和考研派微信公众号(里面有非常多的免费考研资源可以领取哦)[武汉音乐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联系方式] [武汉音乐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简介] [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作曲系录音艺术教研室简介] [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视唱练耳教研室简介] [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音乐基础理论教研室简介] [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作曲配器教研室简介]
为你答疑,送资源

95%的同学还阅读了: [2021武汉音乐学院研究生招生] [武汉音乐学院王牌专业排名] [武汉音乐学院考研难吗] [武汉音乐学院考研群] [武汉音乐学院研究生学费] [武汉音乐学院研究生奖学金] [武汉音乐学院研究生辅导] [武汉音乐学院在职研究生招生简章] [考研国家线[2006-2020]] [2021年考研时间:报名日期和考试时间]
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西方音乐史简介正文
韶华似水,岁月不居。时光老人的脚步终于迈过了世纪之交的门槛,让人们得以静下心来,对刚刚成为历史的百年进行认真思考。其实就音乐界而言,类似的思考早就开始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伊始,仿佛暗中较着劲儿,国际音乐界的理论家们就纷纷撰文讲学,著书立说,迫不及待地要对20世纪音乐进行回顾与总结,有人甚至雄心勃勃地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摆在笔者面前这本厚重的德文书,就是这类著作中的一部。这本书叫《从原始创作冲动到艺术作品:20世纪音乐的作曲过程》,长达419页,是一部论文集⑴。1987年秋至1989年春,德国汉诺威音乐与戏剧学院有计划地邀请著名学者前去讲学,对此专题发表见解,这本文集就是他们讲学的精粹。著名音乐学家赫尔曼·达努舍尔(Hermann Danuser)是两位编者之一,他的论文《灵感·理性·或然性》(Inspiration, Rationalität, Zufall)被置于卷首,起着代序的作用。达努舍尔提出,作曲家的原始创作冲动是如何导致完整的音乐艺术作品的?20世纪音乐代表人物的作曲过程究竟如何?这两个问题正是这本书打算回答的问题。
达努舍尔认为,20世纪音乐有“传统”、“现代”和“先锋”三个范畴,它们从历史角度反映了新旧之间的连接。三范畴是相互独立的三个领域,其代表人物分别为德国的汉斯·普菲茨纳,法国的皮埃尔·布莱兹和美国的约翰·凯奇。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三个领域代表着三种力量,它们实际上存在于20世纪的所有音乐作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是互相矛盾、然而又是不可能相互独立的。达努舍尔以其三范畴说推出了他的中心论题,即建立20世纪音乐的音乐诗学(musical poetics)。由于他的音乐诗学包括过去和现在两个方面,他计划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由权威学者用语文学手段为本世纪已故的大师重建创作过程,是为“客观诗学”(objective poetics);二是由目前仍健在的作曲家对自己的音乐创作过程亲自进行描述与剖析,是为“自陈诗学”(explicit poetics)。
本书的第一部分为客观诗学,包括14篇论文,论及20世纪中叶以前的已故作曲家。汉诺威音乐与戏剧学院原计划邀请一批知名作曲家参加自陈诗学的课题,但因不少被邀请者未能按期成行,这类文章相对较少,书的体例不得不作出相应调整:即增设第二部分,是为20世纪音乐综论,收文3篇;第三部分才收入健在作曲家的文章,凡4篇。
二
第一部分论及的人物从世纪之交开始,有德彪西、普契尼、里夏德·斯特劳斯、马勒、里格和普菲茨纳,接着是世纪初和世纪中叶的作曲家,包括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欣德米特及第二维也纳学派的三位代表人物:勋伯格、贝尔格和韦伯恩;最后是两位风格迥异的下一代作曲家达拉皮科拉和齐默尔曼。14篇文章每篇论述一位,风格和体例都不尽相同,各位作者有展示个性和研究成果的充分机会。有的作者着重剖析作曲家某一作品的细节,如德彪西;有的却相当全面而详尽地研讨其整个创作过程,如巴托克。虽然就整体而言这组文章与达努舍尔的企划与期待还有距离,但从单个看它们仍不失为一篇篇颇有吸引力且各具特色的专题研究,对专家和圈中人士无疑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女学者格罗思(Groth)的《克劳德·德彪西:保留一点奥秘》是研究《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的专论。作者在该剧开场的前29小节发现了德彪西经过精心计算的建构方法:即以倾向于均衡性的传统乐句组织开始,然后通过删除对其进行改变,以创造一种不规则的结构。作者以勿庸置疑的证据雄辩地证明,德彪西只有在完全深思熟虑以后,才将他的音乐构想诉诸纸端,从而澄清了某些学者的错误见解。虽然这项研究成果仅来自一部作品的很小部分,但它仍清楚地表明,对德彪西而言,细节是经过仔细计算后才产生的,即使内行也不大可能一眼就辨识出来⑵。
于尔根·梅德尔(Jürgen Maeder)的文章提供了普契尼作曲过程后期的许多信息,特别论及他改编歌剧脚本的过程。作者以大量歌剧脚本手稿为据,论证了普契尼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将18世纪意大利歌剧脚本中盛行的矫揉造作的语言,巧妙地改造成当年晓畅易懂而又符合人物身份的语言的⑶。冈特·卡茨恩贝格(Günter Katzenberger)论斯特劳斯的文章提出了作曲家自己有关原始创作冲动的观念,即二至四节绝对来自灵感的乐思,加上将此乐思变成一复杂乐句之组成部分的艰苦劳动。作者将斯特劳斯原始创作冲动和已发表乐谱之间的中间阶段划为五步进行描述⑷,然后分析斯特劳斯在修改《麦克佩斯》乐器法细部和《埃莱克特拉》演出剧本细节所下的扎实功夫⑸。
达努舍尔论马勒的文章确实体现了他在代序中提出的论点,可说为其他作者提供了一个按他的思路写作的样板。他认真研究与分析了马勒在各种论著中有关创作过程的阐述,从而归纳出马勒的“自陈诗学”,同时推出了他自己重建的“客观诗学”。 达努舍尔将马勒的“自陈诗学”看着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结合,而以后者占主导地位。马勒在完成第九交响曲时写下的名言或许可以看着是这种结合的概括:“我越来越经常地看到,人不是在作曲,而是在被作曲。⑹”达努舍尔还引用了马勒论作曲过程的其他例子:“我作曲时常常从中间开始,常常从开头开始,偶尔甚至从结尾开始;而剩下的部分呢?其实只是围绕着上述材料进行相应的加工,直至整个作品“自圆其说”乃至大功告成⑺。“我的D和弦(第一交响曲第四乐章375小节)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仿佛是从另外一个世界飘忽而来的。⑻”这就颇具中国古代天籁自然天成之神秘意味了。达努舍尔对马勒有关作品的草稿、第一版和其后的版本进行了极其严谨而翔实的研究,并据此将其作曲过程分解成九个步骤。他又以《吕克特歌曲》五首之一的《请别在歌中看我》(Blicke mir nicht in die Lieder)为例,一一校勘了手稿素材、誊正本和印行总谱之间的变更与修改处,从而印证了他的“九步骤”说,很令人信服⑼。
赖纳·卡登巴赫(Rainer Cadenbach)论里格和沃尔夫冈·奥斯托夫(Wolfgang Osthoff)论普菲茨纳的文章表明,这两位作曲家分别代表着德国学者所谓“原始创作冲动”概念的两个极端。一方面,前文认为,“里格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他的同时代人之美学信念那种意义下的原始创作冲动。⑽”对他而言,首次创作冲动似乎淹没在整部乐章的完成之中,“灵感”的概念仿佛受到理性的约束。另一方面,后文认为,普菲茨纳强烈地反映了原始创作冲动的本质,他认为,写一部音乐作品就像写信一样,恰当的形式源于原始音乐冲动并以此为据渐次形成。“所以并不是追求形式的愿望,而是原始创作冲动本身按照其内在的生物学规律,创造了形式。⑾”
福尔克尔·舍尔里斯(Volker Scherliess)以《管乐交响曲》为例,阐明斯特拉文斯基在作曲中使用的方法是纯机械性的。“他的作曲法不是将动机种子展开以生成一个有机的作品整体,而是将作曲前业已备齐的元件排列和组合起来。⑿⒀”
索姆费(Somfai)的文章透辟地阐明了巴托克从原始创作冲动到艺术作品的全过程。作者从巴托克对原始创作冲动持三种不同处理方式的三部作品入手进行分析。1922年创作的《第二小提琴奏鸣曲》是巴托克完全凭头脑构思出来、在创作起始阶段不借助钢琴的少数作品之一。与此相反,1926年的《钢琴奏鸣曲》却是在钢琴上反复即兴演奏、并将新乐思溶入作品的结果。1934年问世的《第五首弦乐四重奏》则体现了从草稿直接转化为誊正本的作曲方法。这三部作品从最初潦草不堪的草稿到最终定稿的完整总谱之间都存在着一系列逐渐演进的创作阶段,就像三个家族不同的繁衍谱系一般。索姆费将三个谱系清晰直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他还简述了匈牙利近年来的巴托克研究成果,其中最重要者将反映在布达佩斯巴托克档案馆计划出版的《巴托克全集》中。作曲家祖国的学者若对这位作曲家进行研究,比起外国学者来无疑有很大的便利条件和优越性,巴托克研究中西方学者的局限性和匈牙利学者的透彻性再次证明了这一点⒁。
吉泽尔黑尔·舒伯特(Giselher Schubert)的文章认为,欣德米特对原始创作冲动这一概念的态度颇为引人注目。欣德米特用“Vision”一词来表达原始创作冲动,并赋予它完全古典主义的定义。Vision在德文和英文中都有幻影、梦幻、想象力、甚至显圣等意义,其含义与“灵感”相当接近。欣德米特将Vision定义为“黑夜雷雨中的一道闪电,它使作曲家能在一刹那间将其力作的音乐全景尽收眼底,不仅看清总的轮廓,而且对每一细节特征都洞察秋毫。⒂”但在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原始创作冲动似乎只是萌芽形式作品的忠实记录,也就是说,作品的誊正本与草稿之间往往只有少许的细节改动。这样,欣德米特作曲过程的研究就变成业已完工的作品的研究了,作曲过程之研究本身则几乎无戏可唱。可以说,Rationalitat (理性)作为作曲技巧之的一种形式在欣德米特原始创作冲动中起着关键作用,虽然技巧永远不可能完全代替Vision,但它毕竟还是一个重要因素。然而欣德米特同时仍承认,如果说作曲技法是人人都可以学会的话,那么清晰的Vision是只为真正才华卓具的作曲家保留的。
研究第二维也纳学派三位作曲家的文章采用了不同的视角。马丁·施密特(Martin Schmidt)论勋伯格的文章简炼精悍而又鞭辟入里,它概述了勋伯格在作曲过程中通常采用的步骤。阐明了他所谓的“基本形状”(basic shape)这一概念及其在音乐形式中的有机实现;并以《第一弦乐四重奏》开头的几个乐句为例,探讨了他的修改过程。谈到原始创作冲动和序列音乐作品之间的关系,施密特指出,对于勋伯格来说,音列不是抽象,不是预作曲(precomposition),而是“与基本形状的具体实现密切关联的。”(an die konkrete gestaltliche Realisierung gebunden⒃)他最后得出结论说,只要深入地研究勋伯格就不难发现,他的作曲过程是深深植根于19世纪西方的传统音乐的。文章还强调了解乐句结构是了解所有勋伯格作品的关键。引人注目的是,施密特的文章没有引用集论方面的文献,相反却参考了不少美国学者的论述⒄。
鲁道夫·斯特凡(Rudolf Stephan)将贝尔格的作曲过程的准备阶段分成三步,一是决定曲式,它常常同时包含两个完全不同的曲式原则;二是依照音乐的对称性决定动机和主题音乐起始乐句的性质;三是产生和声和动机细节以对乐句进行调节。文章列举了贝尔格对《室内协奏曲》的节拍计算和他校勘修改《璐璐》的方法。文章还强调了勋伯格对贝尔格和韦伯恩的影响与激励。与施密特的文章相反,此文没有提及美国学者的著述⒅。
赖因霍尔德·布林克曼(Reinhold Brinkmann)认为,与韦伯恩被研究得很透的十二音作品相比,他的早期作品似乎未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因此他把文章的重点放在早期作品上。1925年以前,韦伯恩创作了不少声乐和器乐作品,但其中许多短小的作品并未出现在后来出版的作品集中,只留有未完成的草稿——它们是被作曲家放弃了。布林克曼据此认为,也许当时韦伯恩在作曲上表现出了某种隐形的无把握性(eine latente Unsicherheit),而当他发现十二音技法以后,这种无把握性的感觉也就烟消云散了。文章对《六首小品曲》op.9进行了极其细致的语言学研究(philological investigation),并以此为例阐明了韦伯恩的作曲方法。对于1925年以后的作品,布林克曼只引用了80年代初的二手文献,也就是说,他没有利用此后由瑞士保罗·萨赫尔基金会(Paul Sacher Foundation)保存的好几本韦伯恩草稿。如仅以《九件乐器协奏曲》op.24为例,草稿本上就有完全不同的五种曲式计划和其他许多虽然零乱、但非常丰富的资料。有些评论家对布林克曼未能对留有较多研究线索的后期作品多下功夫表示惋惜,他们相信,如果这样做了,将反过来促进他的早期作品研究⒆⒇。
迪特里希·肯姆培尔(Dietrich Kamper)论述意大利作曲家达拉皮科拉,着重分析了他的合唱与乐队《解放之歌》,展现了该作品长达五年的作曲演变过程(1951-1955)。文章还通过共同的序列技法这一视点,探讨了这部作品与完成于1952年的钢琴曲集《安娜莉贝拉的音乐扎记》之间的关系,指出了达拉皮科拉音乐中的某些序列和数学特点。
武尔夫·科诺尔德(Wulf Konold)论齐默尔曼的文章收罗了大量有关表演问题的信息及齐默尔曼对这些问题的反应,同时讨论了他创作过程的一些技术问题,然而几乎没有提及他作品中的原始创作冲动,更不用说对它进行探讨了。
三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收入三篇文章,主要讨论音乐的社会反映及其与其他表演艺术之间的共同性,其读者面似乎与第一部分不尽相同。克劳斯-恩斯特·贝纳(Klaus-Ernst Behne)认为,作曲过程原则上是作品被人们所接受之过程的反映(21)。可见贝纳实际上是以听众的美学反应标准来衡量作品之成败的,为此他把20世纪西欧乐坛的作品分为两类,一类更直观地源于先前的音乐经验,另一类则在更大程度上是技术和机械化程序的产物。贝纳竟把整个十二音运动称之为“作曲家的伪作坊理论”,(false working place theory of composers)(22)并据此将第二维也纳学派与1950年后的序列作品列为一类。这就为所有的序列音乐设置了一个人为的、统一的聆听价值标准,从而忽视了体现勋伯格、贝尔格和韦伯恩之实质的乐句建构模式与以布莱兹和斯托克豪森为代表的一批作曲家之规则系统(algorithmic)方法之间的区别。贝纳的两类说及其结论似乎与第一部分大多数文章的论点大有径庭。
第二部分的第二篇文章出自彼得·霍斯特·纽曼(Peter Horst Neumann)的手笔。他探讨了“灵感”(inspiration)这一概念及其与“创造性”(creativity)概念之间的关系,后者不是一般意义下的创造性概念,而是分别由普菲茨纳、勋伯格和作家托马斯·曼提出来的这一概念。他以普菲茨纳完成于1917年的歌剧《帕莱斯特里那》和勋伯格完成于1910-1913年的配乐戏剧《幸运之手》为例,对两者进行了比较。前者视野保守,因而在乐音的组合上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后者则强调“艺术不是胡拼乱凑,而是‘幸运之手’创造出来的。”(art is not concoction but the creation of a “fortunate hand ”)(23)文章还跨越艺术范畴之鸿沟,以托马斯·曼完成于1947年的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Doktor Faustus)为例,进一步分析与阐明了这种差异。
在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篇文章中,耶尔格·齐默尔曼(Jorg Zimmermann)将理论家们的论点归纳成一部“三部曲”:一是保罗·塞扎纳的概念——艺术是与自然平行的和谐;二是马克斯·恩斯特的“对本质上平淡无奇之现实的一个偶然巧合或蓄意为之的巧合进行系统的发掘”;三是马塞尔·杜坎姆普的论点,他把艺术设想为“我们日常生存的一个如此安排好的共同要素,以致设计好的目的会在一个新观点后面消失殆尽。”该文作者以此来总结20世纪造型艺术的发展过程,有些评论家认为,这与达努舍尔的三范畴说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
本书的最后部分收入四位作曲家按达努舍尔的企划撰写的四篇文章,可以看着是所谓“自陈诗学”的尝试,但四文的体例与表述方式却迥然不同。对于作曲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合这一问题,莱因哈德·费伯尔(Reinhard Feobl)阐述了自己的某些想法。他的文体别具一格,整篇文章由一个个格言与警句组成,当然加上了他自己的引申与发挥。阿尔弗雷德·克彭(Alfred Koerppen)的文章较具方法论色彩,他运用与第一部分大多数文章相伯仲的语文学方法,为他的听众描述了自己的作曲过程。他的“自陈诗学”似乎与上述“客观诗学”没有太大的差别。西格弗里德·马特乌斯(Siegfried Matthus)以自传和编年体方式概述了自己对作曲创作艺术不断积累的体验。他对创作过程中天才的概念提出怀疑,明白表示自己的作曲创作活动与其他任何行当的工作并无差别。沃尔夫冈·里姆(Wolfgang Rihm)在文中使用的主语“我”(Je)实质上代表现代包装下的天才概念。比如说,里姆的中心论点就与贝纳的音乐美学观点完全不同。里姆认为,一切所需要的乐音早已存在着,它们只不过等待着作曲家去发现而已。他还认为,声音早已存在于作曲家的生活之中,而勋伯格的方法不过是这种声音一种被体验之音质的名字,或者符号。他是以这种意义来谈及时间的,即现在、过去、将来在同时刻同时存在。里姆用一个隐喻来总结他的文章:“当一个植物长成一个可以辨认的圆点时,整个植物都生长了。(24)”
五
本书诸位作者对20世纪一批重要作曲家的作曲过程进行了研究,或探讨了音乐与社会、音乐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关系,或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剖析;提出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新研究思路和新研究方法,发现了不少过去尚未发现的东西,对当代作曲家颇有借鉴和参考价值。从这个意义看来,这无疑是一本值得重视的好书。但20世纪音乐诗学是一个大题目,很难想象这本文集能够对整个课题给出圆满答案;名字叫得越大,被勾起的期望值越高,但往往“盛名之下,其实难付”。从这个意义来说,如果人们读过此书后产生些许遗憾或失望感,那也是在情理之中。
《诗学》(Poetics)是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335年写得一篇权威论文,对作为模仿艺术的诗艺立下了定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都认为,诗歌、音乐、舞蹈、绘画和雕塑均以模仿为其共同原则,彼此间的区别仅在于模仿的手段不同(如颜色和声音)、对象不同、方式不同而已。要模仿的对象即是行动中的人。《诗学》第一卷的各种模仿诗歌是根据模仿的手段、目的、方法、效果加以区别的。第一卷还对悲剧进行了精辟的论述。西方关于诗歌的扛鼎之作还有法国人布瓦洛1683年发表的《诗艺》(L’ Art poétique)。上述著作特别是《诗学》在西方知识界几乎有着神圣的地位,任何僭越都会引起人们的反感。
斯特拉文斯基无疑是伟大的作曲家,1939年九十月间,他刚刚移居美国,就应邀在哈佛大学新落成的演讲大厅发表学术演讲,内容是有关音乐作曲和理论的六篇讲义。还在欧陆的时候,他就在他人的帮助下准备好了法文讲稿;他是有备而来,用法语讲学的。演讲获得了成功。1942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将讲稿出版,书名《音乐诗学》(Poétique musicale)。虽然这本书受到了欢迎,评论界也承认其学术价值,但颇有微词的仍不乏其人,一般认为书名的口气未免太大,因为它并非对整个音乐的“诗学”进行令人信服的全面描述。
达努舍尔在书名中提出“20世纪音乐的作曲过程”,又在代序中表达了建立“20世纪音乐诗学”的勃勃雄心,这当然无可厚非。问题是仅仅从这本书看来,还远远不够份量。20世纪音乐是个很大的概念,要对其进行全面描述首先要选定20世纪最杰出和最有代表性的音乐家。达努舍尔提出,普菲茨纳,布莱兹和凯奇是“传统”、“现代”和“先锋”三个音乐范畴的代表,遗憾的是,连三位代表人物都有两位没有涉及,更遑论其他的重要作曲家了。由于组织者和主编都是德国人,这就在选题上带来一定的局限性,表现在德籍作曲家比例过大,而英、美、俄、北欧、东欧等地作曲家则相对缺乏;完全没有提及的20世纪大师则有西贝柳斯、拉赫玛尼诺夫、普罗科菲耶夫、米约、格什温、科普兰、哈恰图良、肖斯塔科维奇、布里顿等人。不去研究这些人谈何20世纪音乐作曲!另一方面,“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因此对于“自陈诗学”作曲家的遴选,应以健在的大师级人物、或者至少潜在的大师级人物为准;其他人物的自我分析仅可作为参考或对照。当然,我们并非要求将20世纪的作曲家一一排队,对他们进行拉网式的调查,并将研究结果事无巨细地罗列出来,那样是低层次的资料堆积。恰恰相反,学术界需要的是在对大师们进行研究、分析和归纳的基础上,寻求规律性和带有结论性的东西。
就方法论而言,在国际学术界,百家争鸣的大门是永远为一切严肃学者敞开的。达努舍尔虽系一家之言,但他提出的原则和模式确有可取之处;他对马勒的研究不仅令人信服,而且对整个课题具有指导意义。可以设想,如果各位作者都遵照他的原则工作,我们将得到一本质量高得多的书。遗憾的是,情况不是这样。在“客观诗学”的14项研究中,或许只有索姆费的巴托克研究是个例外,它比较严格地遵循了达努舍尔原则,其成果受到学术界的较高评价。其他文章则我行我素,各有方法、各具特色,单独看来都是好论文,但组合起来就很难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了。从这个角度看,它们似乎只是有待进一步梳理和深加工的素材。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也是如此。整本文集证明这项学术课题的组织是松散的,缺乏紧密的内部协调,因而其结果也只能是初步的、非决定性的。也许课题组织者的初衷就是如此。他们或许还有更长远的计划也未可知,若果真如此,我们当拭目以待,而现在则不必苛求。
国际诗歌界的诗人与理论家、匈牙利人卡尔曼·卡洛齐博士(Dr. Kálmán Kalocsay)和法国学者加斯顿·瓦伦铿(Gaston Waringhien)及英国学者罗杰·伯纳德 (Roger Bernard) 合作,完成了一本权威的诗歌理论著作(25)。这本书包括格律学、诗艺和韵书三部分,可总共才158页。由此可见,经典著作并不一定要大部头,经得起时间长河大浪淘沙的过硬质量才是根本。卡洛齐的《诗艺》(La Arto Poetika)是部理论著作,但本身却是一部由六部分组成的长诗,在节奏、音节数和韵脚方面极其严谨,自始至终毫发不爽。他写完后已经精疲力尽了,但仿佛意犹未尽,又用法国的ballade(三节联韵诗格)写了一首带有戏谑意味的小诗,作为全书的代序。这ballade在音乐中叫叙事曲,是为钢琴或乐队谱写的不拘一格而又富有浪漫气息的器乐曲。同一词汇在诗歌和音乐两个领域同时存在并具有相近的含义,这里的象征意义在于,音乐和诗歌的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息息相通的。他的ballade的最后“献词”是:
诗歌王子,请武装起来!
或者悲歌一曲,含泪祷告,
或者像蟋蟀那样,欢乐鸣叫!
我们给了你一切,除了天才。
好一个“我们给了你一切,除了天才”!这委婉地道出了理论著作、即使是经典理论著作的局限性。无庸讳言,创造性艺术是需要天才的。古往今来,世界上熟悉诗学或作曲法的人何止万千,但能让人们记住的诗人或作曲家却寥若晨星。比起文学和诗歌来,音乐无疑更具有专业性。如果说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如高尔基可以成为一流作家的话,很难想象对和声和曲式完全外行的人可以成为一流作曲家。从这个意义来讲,音乐比文学和诗歌更加需要理论著作。尽管有局限性,但谁也否定不了理论著作的决定性指导意义。在诗歌理论著作已经很成熟的情况下,我们期待着她的姐妹艺术——音乐——除经典的理论著作外,也拥有像“音乐诗学”和“20世纪音乐诗学”一类新兴的理论著作。我们当然不愿意仅仅满足于名号,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与其名号相符合的理论著作。
———————————————————
参考文献
⑴Vom Einfall zum Kunstwerk: Der Kompositionsprozess in der Musik des 20. Jahrhunderts, ed. Hermann Danuser & Günter Katzenberger, Laaber, 1993.
⑵Debussy Studies, ed. Richard Langham Smith, New York, 1997.
⑶The Puccini Companion, ed. William Weaver & Simonetta Puccini, New York, 1994.
⑷同⑴ p.68.
⑸Michael Kennedy, Richard Strauss: Man, Musician, Enigma, Cambridge, 1999.
⑹同⑴ p.91.
⑺Ibid.
⑻同⑴ p.88.
⑼The Mahler Companion, ed. Donald Mitchell & Andrew Nichol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⑽同⑴ p.103.
⑾同⑴ p.142.
⑿同⑴ p.182.
⒀Stravinsky Retrospectives, ed. Ethan Haimo & Paul Johnson, London, 1997.
⒁The Bartók Companion, ed. Malcolm Gillies, OR: Amadeus Press, 1994.
⒂同⑴ p.235.
⒃同⑴ p.249.
⒄Schoenberg and his World, ed. Walter Frisch, Princeton, 1999.
⒅Thomas F. Ertelt, Alban Bergs ‘Lulu’: Quellenstudien und Beiträge zur Analyse, Vienna, 1993.
⒆Webern Studies, ed. Kathryn Bailey, Cambridge, 1996.
⒇Graham H. Phipps, Book Review, Notes, li (1995), pp.895-899.
(21)同⑴ p.317.
(22)同⑴ p.319.
(23)同⑴ p.338.
(24)同⑴ p.419.
(25) Kálmán Kalocsay, Gaston Waringhien and Roger Bernard, Parnasa Gvidlibro, Warszawa, 1968.
本文来源:http://m.okaoyan.com/whylxy/yjsy_3171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