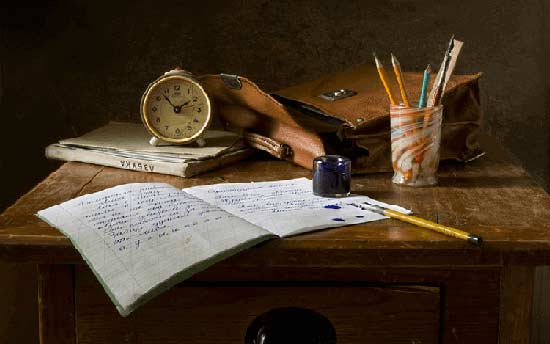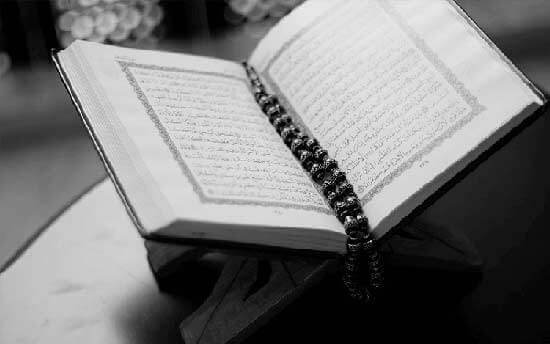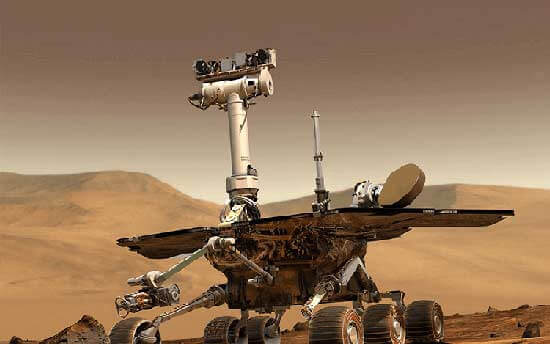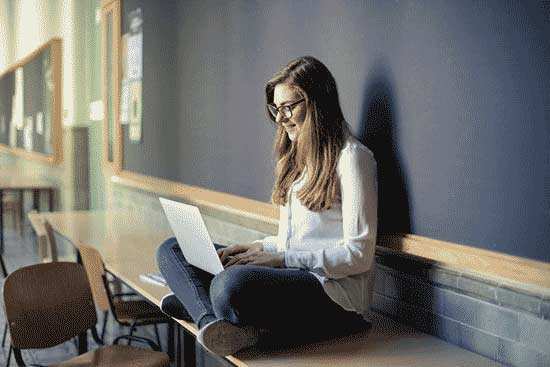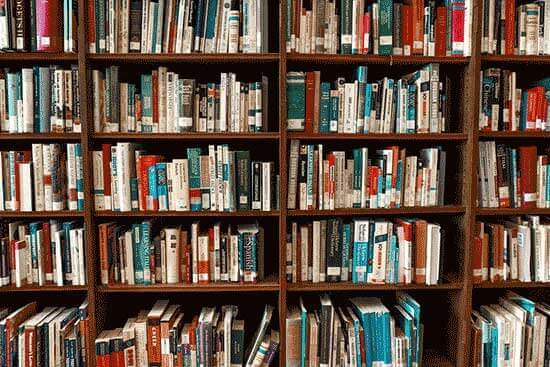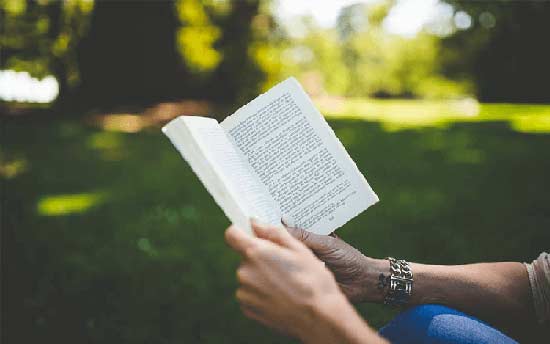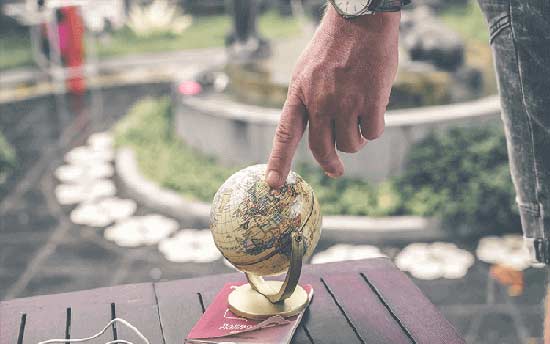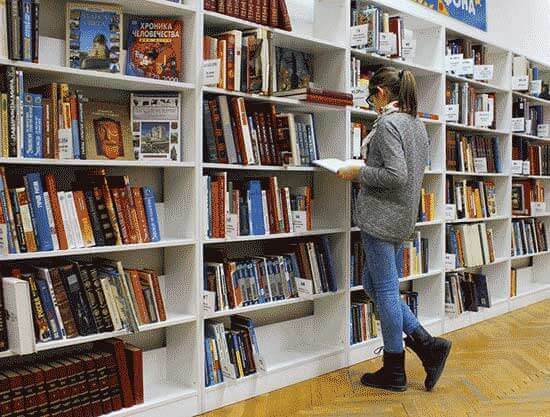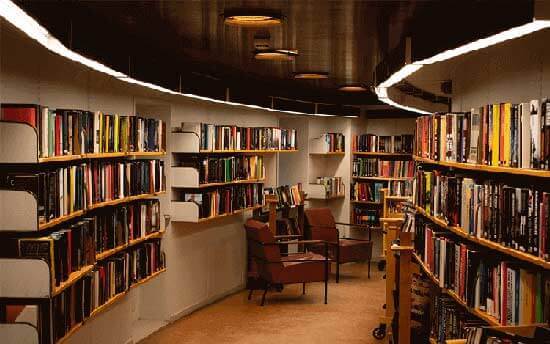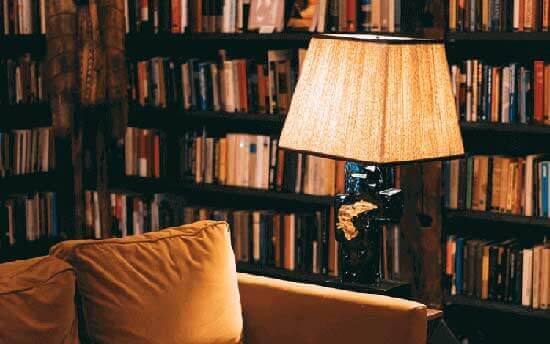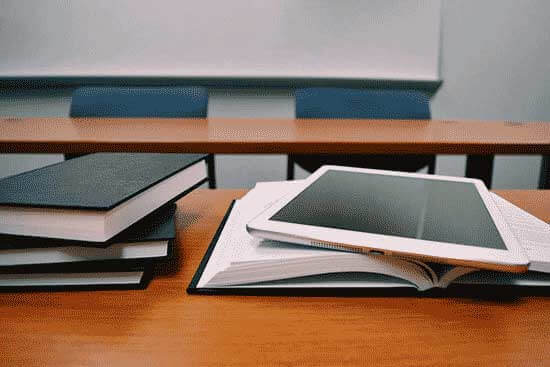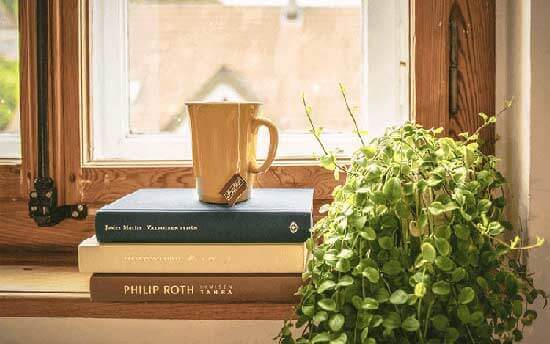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音乐史简介的内容如下,更多考研资讯请关注我们考研派网站的更新!敬请收藏本站。或下载我们的考研派APP和考研派微信公众号(里面有非常多的免费考研资源可以领取哦)[武汉音乐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联系方式] [武汉音乐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简介] [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作曲系录音艺术教研室简介] [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视唱练耳教研室简介] [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音乐基础理论教研室简介] [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作曲配器教研室简介]
为你答疑,送资源

95%的同学还阅读了: [2021武汉音乐学院研究生招生] [武汉音乐学院王牌专业排名] [武汉音乐学院考研难吗] [武汉音乐学院考研群] [武汉音乐学院研究生学费] [武汉音乐学院研究生奖学金] [武汉音乐学院研究生辅导] [武汉音乐学院在职研究生招生简章] [考研国家线[2006-2020]] [2021年考研时间:报名日期和考试时间]
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音乐史简介正文
中国的古代历史文献极为丰富,因此传统的历史学研究自然会以历史文献为主要材料。随着学术的发展,历史学家对文献的认识更加全面和客观,对历史研究也提出了一些新方法、新理论。疑古辨伪在中国几百年的学术发展史上有着一定的传统。五四时期,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相互碰撞、彼此融合,在此背景之下,以顾颉刚、钱玄同、胡适为代表的中国学者(被称为“疑古派”)再次掀起了一股疑古思潮,他们质疑旧古史,对旧古史系统发出了全面挑战,提出了“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著名口号。
围绕古史的研究,顾颉刚先生曾开展过一系列的民俗学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对孟姜女故事流变的考证。他在对民间传说故事、民间歌谣的整理时发现,这些民间传说故事或歌谣在流传的过程中,从形式到内容甚至意思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他的民俗学研究成果表明,古代史事的流传具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带有不同人们的主观因素,打上不同时代的历史烙印。他将自己的民俗学研究成果作为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的力证之一。
在大量研究实践的基础上,顾颉刚先生提出了新的史学研究思路和方法,那就是打破学科界限,将民俗学引入到历史学研究中,将两个领域相互联系,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他认为要研究古史的内部含义,解释古代史话的意义,必须要借助民俗学的研究。他为自己拟定的一套古史研究计划,体现出他治史的史料观和方法论:就史料而言,涉及文献材料、实物材料和传说;就研究步骤和方法而言,首先从古代史书考辨入手并加以系统,其后用实物印证古书中系统出的古史,最后用民俗学研究成果研究传说古史,了解真实状况。不难看出,顾颉刚先生已经非常明确地将民俗资料和民俗学研究作为古史研究的又一有力旁证和研究方法。可以说,史学研究中吸纳民俗学研究,是继王国维先生提出的将纸上之材与地下之材相互印证、互为补充的“二重证据”法之后,提出的又一个具有创新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历史研究思路和方法,堪称古史研究的第三种“证据”。
与顾颉刚先生这一治史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是,音乐学家黄翔鹏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方面的创见。
与传统的历史学研究相似,以往的音乐史研究仍然是仅从文献到文献。但是,文献的弊端已显而易见,其中存在的主观人为因素不容忽视:从内容上看,文献所记之事不可能全面而完整,所记内容的选择具有主观性;从时间上看,文献所记内容的时间段与人类漫长的历史相比,仅是很短的历史阶段,很多未可知的内容不被记录在案;古书在破、旧、散后,会经人传抄,在此过程中,其内容的完整性和正确性都会大打折扣;此外,由于古代掌握记史权利的史官大多对音乐实践知之甚少,而又难以“不耻下问”,因此文献中的音乐记录多晦涩难懂,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我们正确地认识古代音乐。随着音乐考古学学科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它在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作用日益凸现出来。大量的音乐考古发现和研究不仅能证明文献记载的音乐内容、纠正其中的错误、补充其中的缺漏,还能拓宽我们的视野,将古代音乐历史的开端不断提前,从而创写音乐史。音乐被称为时间的艺术,它不可逆转,古代没有录音设备,因而古乐无法留存至今。保留至今的古代乐谱是古代音乐的一种符号记录或载体,考古发掘出土古代乐器所保存的音响可谓是古代音乐的“物化形态”,两者无疑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古代音乐基本形态构架的认识,但对于古代音乐的乐调及具体面貌,我们仍难以确知,难道古乐失传了?
黄翔鹏先生就此提出了“古乐埋藏在今乐之中”的著名观点。他认为,“历史上的‘今乐’,事实上是古乐生命的延续,它在传承过程中分别以原始面目、渐变的面目、发展了的面目流传至今。……在变迁中总能保持着本身形态的稳定性。”1这意味着中国古代音乐可能仍然生生不息地存活于民间。
我国晋西南的沿黄河一带的民间音乐存在一种极为特殊的调式结构,即使用完整的七声、八声但均缺少“角”音。无独有偶,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在这一地区的侯马十三号墓中曾出土过一套春秋时期的编钟,经考察发现,这套编钟的音阶结构也缺少“角”音。21978年,湖北随州出土了举世闻名的战国早期曾侯乙钟,这套钟的音乐特征与当地至今犹存的“楚声”存在联系。3可见,中国音乐的传承有着惊人的稳定性,正如先秦孟子所说,“今之乐,犹古之乐也。”
留存至今的民间“遗音”常具有古老的历史渊源,它们不同程度地保存了古乐的面貌。
其一是古老的民俗音乐遗存。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祭祀活动或民族史诗中的音乐,大多能严格传承,至今不变。民俗以人民为主体,由广大人民共同创造和享用,并被广大人民所认同,正是基于这一点,民俗才能在历史长河中葆有惊人的稳定性。古代音乐大多包含于一定的民俗事象中,与民俗事象混生,并随之传承延续而得以留存。例如,仪式中所用的音乐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这一仪式共同“生存”,它与仪式的整体情境和活动目的都密切相关,是仪式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些仪式在民间代代相传,其中特有的音乐也随之保存下来。
其二是在一定封闭性的文化特点中长期保存的民族音乐特征。就民俗文化的传承而言,由于传播者是人,因此其传承状况常会受到传播者自身以及他所处的环境的影响。居于交通便利的平原地带的人们,由于与外界交流广泛,其民俗文化的传承通常会加入更多的新元素,表现出较多的发展性和变异性,但其基本的文化内核仍然蕴涵其中,其音乐的传承则表现为音乐本质特征的稳定性,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中国地域广阔,一些人群长期居于崇山茂林,受地理条件的限制而与外界交流极少,甚至几乎隔绝,他们的生活和文化长期处于半封闭甚至封闭状态,而其民俗文化却能较好地保存下来,他们的音乐也能更为“原貌”地流传于后世。
此外,某些民族或地区的乐种也可以相对完整地保存古代某一曲调或歌曲的原貌等。
这些至今犹存的古代遗音是活的历史材料,被称为古代音乐的“活化石”,它们或保存着古代音乐的原貌,或留有其表象特征,抑或蕴涵其实质内核,是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又一重要材料来源。它们对于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古代乐调及古代音乐形态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堪称音乐史研究的第三种“证据”。研究中,全面而客观地把握现存活的音乐资料的历史渊源,将现存活材料置于历史的状况中,即所谓历时性研究中结合共时性考察,是音乐史研究中吸纳和运用民间活材料的合理思维方式,也是音乐史研究的必然发展趋势。
中国音乐历史的研究,除立足于文献外,应汲取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此外,还应客观合理地搜集和利用民间民俗音乐中蕴藏的古乐“活化石”,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只有将这三者良好地结合,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更加接近古代音乐历史之真实,从而“立体”客观地呈现出中国古代音乐之面貌。
注 释:
1、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115页。
2、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23页。
3、黄翔鹏:《溯流探源》,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73页。
本文来源:http://m.okaoyan.com/whylxy/yjsy_317117.html